文艺批评|敬文东:颂歌,一种用于抵抗的工具——吉狄马加论(下)
点击上方蓝字“文艺批评”关注我们
玛雅学家约翰·梅杰·詹金斯说过:“全球土著人共同信奉的”条律是:“文化如同一个美丽的小孩,从宇宙的中心向外生长,在时间中成熟。”只不过骄横、蛮霸的科学主义,迫使曾经相信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许多民族“在时间中成熟”,敦促它们逐渐“进化”为无神论者,而在大凉山的护佑下,彝人固执地坚守了自己祖传的信仰与记忆,保护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传统、歌喉、天真、诗性和令人震惊的神秘性,让他们有机会继续缅怀祖先的荣光,拒绝“在时间中成熟”和烂熟。诗人吉狄马加深知这种神秘性和彝人血肉与共的深刻关系,自觉认定它必须成为诗歌写作的重心或焦点。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彝族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出于对母语、发源地和祖灵的感恩心理,吉狄马加有理由和他的民族一道,拒绝“在时间中成熟”,继续“固守失落的文明”。被彝人视为神圣之物、必须要得到歌颂的祖灵将存于何处?这些急迫的问题,构成了吉狄马加诗歌写作最为本真的主题、动机、出发点和强劲的内驱力。吉狄马加说:“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对此我深信不疑。”
本文原刊于《民族文学》2011年第6期,此次推送的为未删节全文。
感谢作者敬文东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敬文东
颂歌:一种用于抵抗的工具
(下)
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认为人类起源于火[1],这个经由感恩之情浸泡后不期而至的素朴观点,跟希腊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看法如出一辙——被直观洞见的同一个世界,才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教师。为了更好地谈论火的功用,《勒俄特依》愿意从远古时期的大洪水讲起。它说:大洪水过后,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位名叫居木武吾的人。他躲在木制的柜子里,才在惊涛骇浪中侥幸逃过一劫——无疑,他就是东方的诺亚,有一张黝黑、通红的高地面孔。居木武吾后来智取天神,和天女喜结连理。这种癞蛤蟆吃了天鹅肉的举动,终于激怒了天女不惧洪水的父亲,遭到了来自天神的惩罚和报复。撒加利亚·西琴(Zechria Sitchin)对亚当和夏娃之间的性关系,有一个颇富想象力的解释:做爱意味着“知道”(to know)[2]——在此,“知道”是僭越,是对上帝不允许“知道”的秘密的冒犯和侵占;有趣的是,在古希伯来语中,“认识”(yada)一词的意思也是“做爱”。这种词源学上的共同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对“知道”和“认识”的报复,作为天神实施惩罚的终端产品,居木武吾一口气生下了三个哑巴儿子。天神的意思也许是:父亲“知道”和“认识”到的东西,不能被儿子们所接管或继承。居木武吾最后碰巧“知道”和“认识”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生火烧水,烫洗三个儿子的身体。在火的声援下,儿子们终于开口说话。长子说声“俄底俄夺,成为藏族的始祖”;次子说声“阿兹格叶,成为彝族的始祖”;三子说声“毕子的咯,成为汉族的始祖”[3]。但自打一开始,三个儿子中的每一个人,都搞不清楚另外两个兄弟究竟在说些什么。从表面上看,这是古代彝人有意杜撰出来的另一种性质的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的故事,火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吉狄马加
面对上帝震怒之后语言纷纷割据,各自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不幸局面,博学多识的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竟然十分天真地相信:被上帝打碎的语言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凝聚,而不是分离[4]。很不幸,在古希伯来语中,“巴别”(Babel)一词的意思,恰好是极为不祥的“变乱”;因此,巴别塔最终意味着隔绝、力量分散、误解、仇恨和杀戮。从此,人类的力量再也不可能拧成一股绳,也不可能朝着某个统一的方向高歌猛进。同一性彻底丧失了,曾经的一颗 心,转眼间变做了互相敌对、互相防范的万颗心——其速度,跟上帝酝酿愤怒的“一刹那”恰相等同,而佛说,“一弹指顷有六十五刹那。”钟鸣则异常机智地表述过:“巴别塔是由骨头和被遗忘的语言构成的。”[5]但是,和《圣经》中巴别塔故事的寓意很可能恰相反对,彝人的火,不仅跟创生有关,还跟语言和种族有染;汉、藏、彝三个伟大的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共同的祖先。或许,在火的声援下,《勒俄特依》杜撰的巴别塔故事的寓意恰好是:尽管三个民族言语不通、难以交流,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互仇恨和杀戮,毕竟它们拥有共同的肉身性的祖先,而不是《圣经》暗示的那样,人是上帝用语言创造出来的。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在赞美他的上帝创世时满怀着感恩的心情:“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6]肉身总是倾向于比声音性的言辞更为可靠,也更有说服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大于肉身的真理[7],更何况是被肉身肯定和定义过的真理呢。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对此有过极好的评论:“绝对的孤寂是灵魂无法逃避的命运,唯有我们的躯体才能彼此相见。”[8]《勒俄特依》始终在致力于呼唤最大公约数的世界,绝不允许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一类的解释学惨案探出头来。对于《勒俄特依》的高贵品德,吉狄马加自有赞颂之词:“我好像看见祖先的天菩萨被星星点燃 / 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肌肉是群山的造型 / 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躯体上长出了荞子 / 我好像看见金黄的太阳变成了一盏灯 / 我好像看见土地上有一部古老的日记 / 我好像看见山野里站立着一群沉思者 / 最后我看见一扇门上有四个字:/ 《勒俄特依》”(吉狄马加:《史诗和人》,第206-207页)
从最根本的角度上说,万物有灵论是一种既质朴、又深入骨髓的博爱精神,也是型号最大的人道主义——它提倡对所有生命的敬重,强调不漏掉任何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彝族史诗固执地相信,一切有血的生命(动物)和无血的生命(植物),都出自同一个母亲(即白雪)[9];人和植物、动物拥有共同的源头,相互杀戮和敌视既没有必要,也是显而易见的意图谬误。吉狄马加有过质朴的申说:“我相信我们彝民族万物有灵的哲学思想是根植于我们的古老的历史的。我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森林和群山都充满着亲人般的敬意。在我们古老的观念意识中,人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平等的。”[10]这种跟人的呼吸恰相等同的言辞,完全不同于钱锺书讽刺过的那种“露天传道式的文字”[11],却刚好是对万物有灵论的最佳阐释。而把作为高地思维的万物有灵论和《勒俄特依》给出的珍贵教诲嫁接在一起,很自然地催生出了吉狄马加诗歌写作中异常浓烈的颂歌色彩:诗歌是歌颂,不是仇恨;是赞叹,不是抱怨和愤怒;是追求同一性,不是追求貌似多元的分裂与割据。在诗歌写作的起始处,吉狄马加就表达了要把颂歌推进到底的决心:“我的歌……/ 是献给这养育了我的土地的 / 最深沉的思念……/ 是献给古老民族的 / 一束刚刚开放的花朵……”(吉狄马加:《我的歌》,第3-4页)这种音质的颂歌,是大凉山的馈赠,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回声,决不是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所谓的回光返照——别急,事情才刚刚开始呢。
汉语文学似乎向来缺乏颂歌传统——或许,屈原的《九歌》算是难得的例外,因为它是唱给神灵的歌谣。而献给朝廷、皇帝和权贵人士的阿谀奉承之词,顶多只能算做“马屁诗”,一种过早诞生于华夏文化圈的特殊诗体,连李白、杜甫那样的头脑和人格也没能幸免于难[12]。颂歌似乎更主要是西方的传统:“在西方文学中,颂歌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古希腊的Hymnos。这是古希腊宗教礼拜的颂神歌……第二阶段:中世纪的Hymnus,歌颂上帝、圣母、圣徒的颂歌……第三阶段:现代的Hymne……自18世纪起,由克洛卜施托克(F.G.Klopstock)首创的一种自由韵律体的颂歌成为现代Hymne的主要形式,此时,神、神灵、英雄、君王、抽象的美德和概念、自然、神圣、崇高的情感等都是颂歌的歌颂对象”,但无论有多少发展阶段和变体,颂歌的重心仍然必须要落实在“对神的歌颂”上[13]。从总体观察,汉民族的心性似乎更倾向于无神论,离作为低地思维的实用理性更近一些;残存于民间旮旯里的万物有灵论,仅仅是观念进化史上被遗忘的死角,类似于人体上可有可无的盲肠。汉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既功利,又具有浓厚的即兴特色——“临时抱佛脚”之类的俗语,道出了宗教消费上的一次性,当然,那是无数个量子一样互不关联的一次性。他们很善于跟各种神祇讨价还价,直到最后相互妥协、订立契约;而被汉人广泛信奉的佛教,恰好是一种反宗教性质的宗教——因为佛教的殿堂上没有神祇,只有跟智慧接壤的觉悟。西方的颂歌是对超验感觉的语言化;汉人却因为“绝地天通”的过早到来[14],过早失去了对超验之物的体悟,真正的颂歌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剩下的,只有唱给权贵的赞美诗,熨贴着身居高位者的耳朵和心脏,顶多只能算做心理按摩术——从《诗经》开始,权贵就是“马屁诗”的春药,宛若权力是大汉男人们的催情剂。吉狄马加,这个用汉语写作的诺苏彝人,依靠他的民族文化传统,给现代汉语增添了感恩和颂扬的珍贵音势,而且,在得到万物有灵论和《勒俄特依》的支持后,他的音势真诚、自然,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矫情成分。他的每一首诗都是颂歌,每一个句子都是颂歌的分子式,每一个词语,都是催促颂歌诞生的基因片段。法兰西诗人雅克·达拉斯(Jacques Darras)在面对吉狄马加的诗歌时慧眼独具:“他背靠着整个彝民族。它赋予他几乎永恒的时间意义,以及他高山的视力,高山上雄鹰的视力,明察平原上的现代变化。”[15]和西方颂歌凭靠的思想资源相比,吉狄马加凭借的,很可能更有资格称得上无限丰富:有万物有灵论助阵,他心中所想、眼中所见的所有事物,都是超验的神灵,都值得歌颂,他因此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可以用于挥霍,近世以来不断被西方人诅咒的“无边的苦海”(a sea of troubles)[16],在诺苏彝人的后代那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有《勒俄特依》撑腰,吉狄马加有能力理解所有不同的种族,因为他们都是他的远房亲戚或兄弟。鹰的子孙,大凉山的后代,火的被庇护者,彝人吉狄马加,总是在致力于歌颂土地、群山、河流、大凉山的斗牛、彝族同胞、故乡、少女……他歌颂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赋予一切事物——哪怕是残废了的事物——以美好、超验的要素,诚如他真诚的表述:“一个诗人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中捕捉到人类心灵中最值得感动的、一碰即碎的、最温柔的部分;”而赞颂,他说,“从来就是我的诗歌的主题”[17]。
在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内部,始终涌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颓废主义暗流。庄子无疑是最大、最深刻的颓废主义者,《世说新语》则是颓废主义者最卓越的集中营,南北朝呢,恰好是文人士大夫集体颓废、专心溃烂的年代[18],在朱姓皇室的统领下,明末江南的士子,把当时所有可能出现的性病,全部自我加冕般请到自己身上,一时间,像遥远的南北朝一样,“床第之言,扬于大庭”[19]——很可惜,艾滋病还没来得及被发明出来,无法被他们尽情享用,更没能给他们收获极端体验的机会。很显然,所有的颓废主义者“都是骨子里的失败者”,只不过“和其他样态的失败者不同”,他们都是些“笑着的失败者”[20]。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美学风格,颓废自有它非常迷人的一面,以致于有人愿意主动为它鼓掌、喝彩:颓废“是一种艺术化的精神状态,以艺术化的个性活动方式对抗社会并进行超越,超越现实社会的矛盾但并不追求升华;以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反抗生命并拒绝崇尚生命的威严,尊重生命的行动力……颓废只是用非升华的方式来获取解除来自社会压抑的可能,用艺术化的创造来实现人生之醉”[21]。但是,作为一种迷人的美学风格,颓废也恰如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痛斥过的那样,“无非是艺术达到了极端成熟的地步,这种成熟乃老迈文明西斜的太阳所致,”颓废表征着“神经 官能症的幽微密语,腐朽激情的临终表白,以及正在走向疯狂的强迫症的幻觉”[22]。必须要感谢大凉山的深仁厚爱,因为它让仅仅陶醉于直观洞见、拒绝“成熟”和“烂熟”的彝族文化,至今仍然以它的古老反而显得格外年轻和英姿飒爽,它的天真直接等同于儿童纯净和充满好奇心的小眼睛。有《勒俄特依》和万物有灵论做后盾,颂歌仍然是颓废和颓废主义的天敌:万物有灵论相信每一种事物都有灵性,万物在暗中发愿、暗中生长,依靠各自的规则,精心培育它们的品格,不允许违背自然本性;《勒俄特依》则努力培植超越种族的友爱精神——这都是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或情绪,坚决反对各式各样的虚无主义。所谓虚无主义,耿占春无疑给出了最精确的界定:它是“生命延续性和连续性意识的丧失”[23]。背靠彝族文化传统和大凉山的吉狄马加,不允许自己笔下流露出任何一个沾染颓废基因的句子;在他的诗歌写作中,即使是死亡,也是积极的、向上的、可以被饱飨的:“我了解葬礼,/ 我了解大山里彝人古老的葬礼。/ (在一条黑色的河流上,/ 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吉狄马加:《黑色河流》,第28页)“总会有这么一天 / 我的灵魂也会飞向 / 这片星光下的土地……/ 那时我彝人的头颅 / 将和祖先们的头颅靠在一起 / 用最古老的彝语 / 诉说对往昔的思念……/ 用那无形的嘴倾诉 / 人的善良和人的友爱……”(吉狄马加:《故乡的火葬地》,第134页)面对死亡尚且从容自若,甚至连死亡都值得歌颂,颓废败于颂歌之手,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华夏文明中的颓废,既有“情之所钟,正在我辈”[24]的炽热,也有“死便埋我”[25]的深刻绝望。归根结蒂,颓废来源于人的孤岛感觉——每个人都是孤岛,彼此互不理解,彼此间大门紧闭,只有在虚无主义的支持下,在颓废和放纵中,发现美和人生的意义。在汉人持久不变的意识中,生命必然通往死亡,死亡则是生命的绝对终结,是颓废的彻底结束,终将归于永恒的虚无,灵魂是不存在的,因此,“人死如灯灭”。《列子》说:“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26]对于汉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在灵界等待“行人”成为“归人”的祖先;或许,德意志的天才少年毕希纳(Georg Buchner),已经代替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个人只是波浪上的泡沫……”[27]
巴别塔的寓意再清楚不过:统一的语言被上帝打碎后,人们纷纷团结在各自母语的周围,种族间的广泛误解,似乎就是必然会降临的事情;诺斯洛普·弗莱关于语言功能的判断既对又错:语言分裂确实阻碍了种族间的交流,以致于“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极难展开,但分裂的种族也暗含着对交流的渴望,至少,对孤岛感觉的深刻恐惧,对接踵而至的颓废主义,是每个种族、每个个体都愿意摈除的东西,但摈除需要来自同类的安慰,而安慰,则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它称作神秘的“语言本身”[28],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把它当做可用于合理交往的“理想的语言环境”[29]。大凉山的厚爱,鹰对自由的向往,火的温暖、仁慈和它拥有的“普遍解释的原则”,一句话,高地思维给了吉狄马加抵制颓废和实施博爱的观念基础,《勒俄特依》则从肉身性的角度,给了他“所有种族都是兄弟”的珍贵启迪。因此,颂歌不仅要把积极向上的情绪献给自己的部族,还必须献给全人类,尤其是那些饱受欺凌的种族。
一个诗人仅仅从他人身上认出自己,还远远不够,能从他人身上看到跟自己相同的命运和神性的存在,才算得上难能可贵。吉狄马加写过许多同黑色非洲、棕色拉丁美洲有关的赞美诗,但那也不过是把彝人的万物有灵论和《勒俄特依》给出的启迪,用于整个人类的一次尝试。当一个东方的彝人,眺望地球那边的印第安人(比如人称“玫瑰祖母”的智利巴塔哥尼亚地区卡尔斯卡尔族群中的最后一位印第安人)、破旧的印第安遗址、不幸的印第安诗人(比如萨尔 ·巴列霍)、生长于南美的非印第安诗人(比如巴波罗·聂鲁达、米斯特拉尔)却又始终在讴歌那块令人忧伤的大陆时,彝人吉狄马加首先想到的,是包含着同情与敬仰的哭泣:“蒂亚瓦纳科,印第安大地的肚脐 / 请允许我,在今天 / 为一个种族精神的回归而哭泣!”(吉狄马加:《蒂亚瓦纳科》,第349页)紧接着想到的,是作为象征和值得赞美的泪眼:“面具永远不是奇迹 / 而是它向我们传达的故事 / 最终让这个世界看清了 / 在安第斯山的深处 / 有一汪泪泉!”(吉狄马加:《面具——致塞萨尔·巴列霍》,第351页)最后必须要想到的,则是欲哭无泪中呈现出来的生命之路:“玫瑰祖母,你的死是人类的灾难 / 因为对于我们而言 / 从今以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位 / 名字叫卡尔斯卡尔的印第安人 / 再也找不到你的族群 / 通往生命之乡的那条小路。”(吉狄马加:《玫瑰祖母》,第356页)吉狄马加在遥远的印第安人身上认出了自己,认出了自己的种族,认出了自己的命运,也认出了现代性追剿下正在慢慢消失的神性。在此,颂歌是理解,是悲悯,是感恩,更是对颓废、误解和巴别塔的坚决阻击,是对交流的渴望和期盼,并且以泪水充当装饰。为遥远的邻居流泪,刚好是对万物有灵论进行的最为液体化、最为温柔的阐释。吉狄马加的诗歌举动,令当代拉丁美洲诗人格雷罗(J.M.Briceno Guerrero)感慨不已:“我觉得他的祖先好像在通过一条地下的秘密网络和我的祖先交流……我可以将吉狄马加看作拉丁美洲的诗人,或更确切地说,是全人类的诗人。因为有一种心灵的神圣语言,它在任何历史语言中都找不到表达。”[30]跟韩少功“知识危机是基础性危机”的论断较为不同[31],吉狄马加很可能更愿意相信,误解才是人类最为基本的尴尬情境之一,它引发了仇恨和冷漠,鼓励了战争和杀戮,诱发出了深刻的虚无主义。但颂歌,背靠万物有灵论和《勒俄特依》的感恩音质,完全可能进入有效抵抗误解的最为有力的方式之列,吉狄马加就曾明确说过:“我写诗,是因为我无法理解‘误会’这个词。”[32]这种低音量的誓言之所以来得格外及时和恰到好处,很可能正是在洞穿了尴尬情境的真相之后,尽力为自己的写作寻找内在的依据与合法性。
钟鸣对最近几十年的汉语诗歌写作,有一个准确的评论:“要论诗歌的进步,除了‘词’的胜利,就人性方面,我看是非常晦暗的,犹如骨鲠在喉。”[33]最近几十年来,诗歌在赞美权贵和黑恶势力上,已经不再明火执杖,至少是变得羞涩有加、“犹抱琵琶半遮面”了,但更多、太多的诗作,仍然像“痛说革命家史”一样,在诅咒世界的丑恶,在哀叹命运的不公;诗歌手艺倒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每个人都在潜心算计词语,词语也在被算计中,听取诗人们的指令各从其类,何时立正、稍息,何时走正步、稳扎马步,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但人性的胜利、心智的健全,依然遥遥无期——或许永远都不能得到指望。跟颂歌对音质的特殊要求相呼应,吉狄马加“诗歌中所塑造的语境、语感与彝族古老的格言谚语‘尔比尔吉’如出一辙”[34],诗句单纯、透明,但又宛若宋人陈郁称赞他的同代词人姜白石那样:“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35]他的词汇简单、剔透;词与词之间,只需要极小的摩擦系数,就能很好地相互粘结,不像某些“艺高人大胆”的汉语诗歌,必须依靠极大的摩擦系数,才能彼此吸附,却给人一种相互强奸、随时可能坍塌的怪异感觉。和使用了太多化肥、香精、染料和人造猪板油的诗歌语言相比,吉狄马加质朴、自然、近乎野生的语言方式,和滋生于大凉山的万物有灵论异质同构,跟《勒俄特依》给出的教诲恰相对称,固执地延续着一种最古老的文明,但最终,还是呼应了最质朴的人性观念——先民们最早发现的观念和情感形式,总是倾向于最有生命力,因为它最具有直观洞见的特性。对此,吉狄马加有十分清醒和异常自觉的追求:“我怎么不能写出既具有民族的特点,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怎样真正写出人类的命运,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36]或许,不必皈依宗教,但可以相信神灵的存在,很可能才是连接远古与现代、连接今人与祖先,抵制科学暴力和恢复生活灵性最恰当的方式之一,才是最能解救现代性病症的可能路径之一,因为在比喻的意义上,它最具有本雅明大声称道的“灵韵”(Aura)特性。而保护人类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本身就是为了救治今天——这个有病的、变态的、打满补丁和绷带的今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精辟地认为: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假如还作为一种体系存活于世,就一定有它的现实基础,根本不可能被轻易碾碎[37],因为按照梅洛-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的细致观察,“体系在其姿势上是毫不客气的。”[38]或许,继续艰难地相信万物有灵论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兄弟,才是最大的“人类价值”、最厚重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当真搞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令人惊讶地认为:对少数几个希腊哲学关键词的错误理解,是西方哲学驶入迷途长达两千多年的罪魁祸首,现在,该由他来正本清源、恢复鲜活的希腊思想传统了[39];诺苏彝人的后代吉狄马加则认为,由于某些古老词语的被埋葬,让他有跟祖先失去联系的危险——对于祖先崇拜意识过于浓厚的彝人,这无疑比西方哲学误入歧途更为致命,因为它更关乎个人情怀、个体命运和种族记忆。吉狄马加诗歌的英文译者梅丹里称得上洞若观火:“今天,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诺苏人的山林被大量采伐,让他们失去了和他们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相和谐的生态环境,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阴影和不安,无疑这是现代化在给他们带来新生活的同时所带给他们的一种负面影响。”[40]山林惨遭修理,树木遭遇屠杀,雪族子孙流出了绿色的血液和眼泪……这意味着山精水怪失去了藏身之地,神话在步步退让,它亘古相传的领地被蚕食,高地思维变得岌岌可危,鹰与火泯灭了各自的神性……现代化在步步紧逼,向大凉山推销它的教义,鼓吹功利和实用理性,低地思维大有全面接管和覆盖高地思维的趋势,最大公约数的世界在被迫缩小自己的疆域。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对低地思维有过一剑封喉般的评判:“现代崇拜紧紧包围着新,使其疲于更新。”[41]“疲于更新”最内在的口吻是:对昨天进行轻易的否定,对无神论进行更为彻底的追逐,对古老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实施坚决的反对,就像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讽刺过的那样, 面对诸神的“宏大法度”,渺小的“人却喜欢用拃去衡量”[42]。显然,吉狄马加的担忧再正常不过:“我写诗,是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同自己古老的历史对话,可是我却常常成了哑巴。”[4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呢?因为某些关键的词语,被“紧紧包围着新”的“现代追求”所埋葬,以致于让彝人的后代丧失了用于接头的暗号或口令,变做无法同历史对话的哑巴——这一回,他们是得罪了现代性而不是天神。毫无疑问,词语即视界,词语即眼睛,词语即看见。如今,该由吉狄马加来重新复活那些被埋葬的词语,刮去它们身上厚厚的泥垢,擦亮它们的腰身,让它们重新来到他面前,以便于在被打量、被凝视中,为他带来新的视界、新的视力王国:
我要寻找的词
是祭师梦幻的火
它能召唤逝去的先辈
它能感应万物的灵魂
我要寻找被理葬的词
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那些最隐秘的符号(吉狄马加:《被埋葬的词》,第79-80页)
为着这个宏阔、艰难的目标,吉狄马加急需要把诗歌锻造成功率强劲的词语考古学;诗歌必须成为洛阳铲,并且具有盗墓者的胆量和能力,附带着,还必须拥有“碳—14”甄别地层和年代的本领。没有必要怀疑,每一个被埋葬的词,都有一个特殊的地层和坑口,就看诗歌怎么展开它的工作了。吉狄马加的做法,仍然是依靠他一以贯之的颂歌音质:唯有通过赞美和祈祷,才能逐步接近酣眠于黑暗之中的词汇,才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坑口、发现它的含义,直到让它顶天立地,重新开口说话——颂歌既是抵抗的工具,也是发掘的工具。荷尔德林对此早有教诲:“依于本源而居者 / 终难离弃原位。”[44]吉狄马加则十分动情地说:“苦荞麦啊……/ 你是古老的语言……/ 只有通过你的祈祷 / 我们才能把祝愿之词 / 送到神灵和先辈身边。”(吉狄马加:《苦荞麦》,第77页)面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现代诗中,“自然变成了一些由孤单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客体组成的非连续体”的警告之词[45],吉狄马加极富战略性地改变了颂歌的身位、目的、性质和功能;颂歌临危受命,在完成了对误解和颓废的抵抗后,又承担起词语考古学的新角色。颂歌是接近被埋葬的词汇的必经之路,是独一无二的神器,是海德格尔所谓“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46]。而寻找被埋葬的词语,就是寻找被遗忘、被蚕食的真理,就是对真理的考古和抢救性发掘。吉狄马加在一首跟彝族祭司——“毕摩”——有关的诗中如是写道:“毕摩死的时候 / 母语像一条路被洪水切断 / 所有的词,在瞬间 / 变得苍白无力,失去了本身的意义 / 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故事 / 被凝固成石头,沉默不语”(吉狄马加:《守望毕摩》,第84页)毕摩之死不仅仅意味着肉身的消亡,它更乐于指称的,是某种至关重要的传统的被迫中断。阿库乌雾很抒情地说:“毕摩的嘴是山岩莫名遭到雷劈之后留下的永难弥合的缝,有一种生物必定会从那里生长。”[47]当某种刻骨铭心的传统被打断脊梁和肋骨,行将消失的,不仅是词语和环绕耳廓的音响,更是所有渴望“生长”的事物以及它们的灵魂——万物有灵的观念注定会遭到侵蚀,《勒俄特依》的教诲会被彝人疏远,高地思维则将处于失语状态。当此关键时刻,又该如何更为有效地寻找那些被埋葬的词语呢?
出于情势的急迫,吉狄马加有意放弃了对城市和钢筋水泥的诗歌书写,放弃了时髦的现代性、全球化和它随身携带着的一揽子黑话,只将目光死死盯住大凉山、彝族同胞、古老的历史,还有注定要被现代性蔑视的高地思维:万物有灵论和《勒俄特依》始终寄居在吉狄马加心中,就像起伏不定的高原,始终寄存在苏格兰农民彭斯(Robert Burns)的心中。这情形,有点类似于瓦莱里(Paul Valery)的精辟之言:“艺术家与他的任意性密切相处,也生活在对他的必然性的期待中。”[48]但跟瓦莱里的所指很不相同,对于彝人吉狄马加,所谓“任意性”,就是全球化和现代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现代人对变化和新事物的疯狂追逐,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早就对现代性有过深刻的指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49];所谓“必然性”,就是彝人心中那个恒定不变的文化常量。如果一位汉族诗人以这种方式展开写作,必将被很多人斥为虚伪和不及物,会被指控为无视时代的变化、不考虑新经验的不断诞生,因为据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新的经验总是在等待新的诗人。经由某个颇富“莫须有”性质的机构授权,今天的汉族诗人似乎有权力和义务在诗歌写作中,热情接纳新经验、折射人在新经验面前新的灵魂反应——最近一百多年来,汉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对现代性展开追逐,就是要和世界接轨、跟世界同步、和滚滚向“前”的世界历史车轮一道滚向“前”去,因此不怕被同化,就怕不被同化。吉狄马加则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彝民族的歌谣和口头文学的摇篮里度过的。那里有我无数的梦想和美丽的回忆。我承认是这块彝语叫古洪木底的神奇土地养育了我,是这样有歌、有巫术、有魔幻、有梦与现实相交融的土地给了我创作的源泉和灵感。”[50]但这种性质的申说,是否能给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自动授予免遭指控的豁免权?耿占春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阅读与阐释吉狄马加的诗使人置身于一种相互交织的语境之中。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不能只在现代主义的修辞风格框架内解读。吉狄马加的诗既置身于汉语写作的场域,又显然植根于彝族经书、神话、民间故事的地方传统,在文本上体现出现代诗与民间谣曲、民族史诗片段的混合风格。”[51]汉族诗人接纳新经验的写作是一种低地写作,吉狄马加则像固守民族传统的同胞那样,坚决实施高地写作,以便于寻找被埋葬的词语。他给予自己的诗歌任务,就是要尽最大努力,抵制新经验对彝民族文化的侵略和污染。作为一个弱小的高地民族,在声势浩大、席卷一切的“全球化”面前,大凉山已经逐渐丧失了它亘古相传的神力,显得极为脆弱。吉狄马加的内心深处之所以有时会“充满着恐惧”,按他的说法,“那是因为我的母语 / 正背离我的嘴唇 / 词根的葬礼如同一道火焰。”[52]他是不是想说,古老的词语也有它自己的火葬?但被火葬的词语能够升天么?吉狄马加似乎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刻意逆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我不在这里,因为还有另一个我,/ 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吉狄马加:《反差》,第19页)而所谓“相反的方向”,就是朝向祖先的方向、大凉山的方向、万物有灵的方向和《勒俄特依》的方向,一句话,被埋葬的词语的方向。更加强劲的词语考古学,来源于勇敢的心性,来自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信赖,也来自于万物有灵论对想象力的鼎力支持——毕竟万物有灵论本身就是想象力的辉煌产物。按照夸特罗其(Angelo Quattrocchi)及其学术伙伴的看法,“想象力正在夺权”[53]——对于诺苏彝人的后裔,想象力是在“夺”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权”。在这场力量过于悬殊的角力中,万物有灵论给了吉狄马加充沛的灵感和想象力;想象力和灵感以它们的充沛和丰盈,则给了作为颂歌的词语考古学莫大的声援,以致于让词语考古学成为双倍的颂歌——这是吉狄马加在应对不断滋生的新经验时,能够享用的最大幸运。充满调皮特性的大凉山、拥有神性的火与鹰,给了他力量;但通过诗歌写作,他也保护了这种力量,让他越来越接近被埋葬的词语寄居的坑口和地层。
构建词语考古学,除了动用祖传的想象力之外,还须仰仗追忆。和想象力同颂歌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追忆决不仅仅是颂歌,还是它的升级形式:追忆要求颂歌更加强劲有力,更加具有温度和湿度,以便更好地忠实于祖先之灵、敦促它和祖灵靠得更近,因为归根到底,被埋葬的词汇,最终掌握在祖先之手;地层和坑口的位置,唯有祖先才知道——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早就教导世人:“起源即目标”。和保罗·纽曼(Pual Newman)所谓“激情本质上是非法的”观点完全相反[54],对于吉狄马加,能够给追忆施以助力的头号种子选手,仍然是催促过人类诞生、让哑巴开口说话的火,是热情的、具有神性和必须得到歌颂的火:“我把词语掷入火焰 / 那是因为只有火焰 / 能让我的词语获得自由 / ……当我把词语 / 掷入火焰的时候 / 我发现火塘边的所有族人 / 正凝视着永恒的黑暗 / 在它的周围,没有叹息。”[55]祖先居住在无边的“黑暗”中,但“黑暗”并非意味着看不见,更不是“明亮”的反面或者后花园,恰恰是“最”“明亮”的意思——只有最明亮的地方,才最需要眼睛具有暗适应的能力:由于强光,人会突然感到两眼一抹黑。这个生理学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作为诗歌关键词的“黑暗”。当词语被火化,顺着它轻盈的升腾方向,“所有族人”都“凝视”着祖先、都看见了祖先——火苗把他们带向了词语的地层和坑口,并照亮了它们。关于火的如许功能,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看得比谁都清楚:“吉狄马加 / 生活在赤裸的语言之家里 / 为了让燃烧继续 / 每每将话语向火中抛去。”[56]火不仅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冲击下继续拥有神性,而且,唯有借助它亘古相传的神性,才能加固追忆的性能,才能提升词语考古学的功率,才能最终通往祖灵永久性的栖居之地——很显然,祖先根本就不可能认识没有神性的火。
感恩是颂歌的核心地带。它起源于对超自然力量的膜拜之情,是对超验的内心体认。在彝人的传统观念中,祖灵及其安息之地,也是超自然力量的组成部分;要想从祖先那里再次找回被埋葬的词汇,激活颂歌的核心部位,让它敏感和兴奋起来,就显得极为关键——毫无疑问,词语考古学的最高果位就是感恩。为了和感恩以及词语考古学相对称,吉狄马加策略性使用了一种很直白的句式:“我承认……”在《献给这个世界的河流》中,他写道:“我承认 / 我曾经歌颂过你……/ 我承认 / 是你创造了最初的神话……/ 我承认,河流!你的美丽曾经无与伦比……”(吉狄马加:《献给这个世界的河流》,第301-302页)他“承认”的,是河流对人类无私的哺育,而“承认”与对河流的感恩之情紧密相连:河流已经不再是自然事物,不仅仅具有物理学属性,它像火和鹰一样充满了神性。和通常的“我相信……”句式相比,“我承认……”显得更为心悦诚服,姿态也更低,抒情主人公和被赞美的对象靠得更近:感恩的本质就是谦卑,就是在神圣事物面前滋生出来的渺小感。在一首写给故乡的诗中,吉狄马加把“我承认……”发挥到了极致:“我承认一切痛苦来自那里 / 我承认一切悲哀来自那里 / 我承认不幸的传说也显得神秘 / 我承认所有的夜晚都充满了忧郁 / 我承认血腥的械斗就发生在那里 / 我承认我十二岁的叔叔曾被亲人们送去抵命 / 我承认单调的日子 / 我承认那些过去的岁月留下的阴影 / 我承认夏夜的星空在瓦板屋顶是格外的迷人 / 我承认诞生/我承认死亡 / 我承认光着身子的孩子爬满了土墙 / 我承认那些平常的生活 / 我承认母亲的笑意里也含着惆怅 / 啊,我承认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 / 纵然有一天我到了富丽堂皇的石姆姆哈 / 我也要哭喊着回到她的怀中”(吉狄马加:《达基沙洛故乡》,第211-212页)吉狄马加“承认”了他必须要“承认”的,无论被“承认”的东西美好还是残忍,只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东西似乎都理应得到承认,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和祖先接头,才能锻造更为结实的词语考古学。事实上,吉狄马加的颂歌以及词语考古学在诗歌中的完成,仰赖的就是“我承认……”这种特殊的句式:它是吉狄马加固守高地写作的原型句法,也是构建颂歌最基本的元素,密布于他的每一首诗作之中,也最为完美地对称于大凉山给出的教诲。原型句法最基本的变体,是吉狄马加特别喜欢的“是”字句:“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 / 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 / 我痛苦的名字 / 我美丽的名字 / 我希望的名字 / 那是一个纺线女人 / 千百年来孕育着的 / 一首属于男人的诗 / 我传统的父亲 / 是男人中的男人 / 人们都叫他支呷阿鲁 / 我不老的母亲 / 是土地上的歌手…… /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 正义和邪恶的抗争 /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 爱情和梦幻的儿孙 /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 一次没有完的婚礼 /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 一切背叛 / 一切忠诚 / 一切生 / 一切死 / 啊,世界,请听我回答 / 我—是—彝—人”(吉狄马加:《自画像》,第5-6页)从“我承认……”向“我是……”转渡,吉狄马加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达力,也为感恩提供了新的装饰物。完全可以倾听这样的解释:由于受到“我承认……”的浸泡,“是”字句更加具有颂歌的功能;有“我承认……”撑腰,最终让寻找被埋葬的词语的工具更为犀利:在祖先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位,更容易接近祖先和祖先们才能掌握的坑口和地层。仰仗这种身位,让吉狄马加无限接近了他的目标:
马鞍终于消失在词语的深处。此时我看见了他们,那些我们没有理由遗忘的先辈和智者,其实,他们已经成为了这片土地自由和尊严的代名词……[57]看见了什么呢?显然是看见了因长期隐藏显得十分僵硬,事实上却又无比活泼的词汇,它们的全部内容包含在一句话中:“我只想给你留下这样一句诗: / 孩子,要热爱人!”(吉狄马加:《这个世界的欢迎词》,第262页)这是彝人的教诲,是最高级别的颂歌,它寄放在大凉山深处,寄放在鹰的翅膀上,也在火的升腾中,它是对一切邪恶的抵抗,也是我们仅有的胜利的强大依据,更是组建最大公约数的世界的基本纲领。这个杰出的纲领,让吉狄马加的诗歌在看似缺少现代韵味的当口,得以从五千年以外来包抄现代性,并把曾经被毁掉的生活在诗歌写作中,给重新组建起来。
2011年3月30日,北京魏公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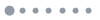
明日推送
毛尖:电影中怎么能少了“二货”?
相关文章
文艺批评 | 姜涛: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
文艺批评 | 张光昕: 挽歌与新雪 ——构想一条当代汉诗的再生线
本期编辑:葡萄菌
文艺批评
听说他们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