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蔡翔:流水三十年
点击上方“文艺批评”关注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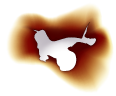
我亲历并见证了这一“三十年”的变化,我也一直在寻找通向未来世界的道路,这一寻找隐蔽在1960年代的记忆之中,至今,我也并未放弃这一寻找,尽管寻找在今天变得怎样的困难重重。我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老去,但在内心深处,仍然回荡着少年时代的呐喊——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始终是共和国的长子。
——蔡翔
编者按
1980年代处于“两个三十年”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对作者蔡翔而言,被唤醒的是1960年代的记忆,这一记忆被压抑在1970年代。那或许是一种有关青春和激情的记忆,一种解放和抗争的记忆,也可能是一种重新创造世界的记忆——有关这一切的记忆,都隐蔽在共和国的理念之中,或者,将它解释为一种“革命”的理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1980年代也是对这一理念的遥远的回应,尤其是有关“异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暗暗接通了1960年代的血脉。在80年代拒绝政治的时候,却隐伏着另一种重新创造政治的愿望。而1990年代更重要的是现实的急剧变化,这一变化才真正使一代人从1980年代的幻觉中走出,直面现实。隐秘已久的1960年代的记忆,这个时候才可能被真正唤醒。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一代,蔡翔老师试图通过对1980年代的讨论,完整地描述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变迁,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找通向未来世界的道路。
感谢作者蔡翔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蔡翔
流水三十年
1982年,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那时,我还在上海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工作,课余无事,乱翻杂志,恰巧读到路遥的《人生》,心有所动,便著此文。文章写好后,投稿给《上海文学》,不久,收到通知,约我去编辑部面谈。在上海巨鹿路675号那座老洋房三楼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我见到了周介人老师,后来又见到了李子云老师,他们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也成了我的引路人。文章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1983年的第一期。再不久,我就调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直到2003年,我才最终离开,到上海大学工作。
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想想,也真有点“弹指一挥间”的感觉。19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即使1990年代,也未免恍如隔世。恍惚间,栩栩如生的,反而是1960和1970年代。也许,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本没有什么“两个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国六十年。后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隐藏在一种共和国的记忆之中。而这一记忆,被反复唤醒,并被形式化。
我想,对许多人来说,1980年代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我也一样。但我以为,1980年代不应该只是1980年代人的纪念馆,它还应该成为一座活着的图书馆,以供人们反复阅读,并不断地征用。重新讨论1980年代,是我目前的一项主要工作,但困难很多。困难之一,恰恰在于自己的新历性,经验有时候反而可能是一种羁绊,甚至是视野和想象的局限。因此,个人的记忆也仅仅只是个人的记忆而已。
我在1980年代的写作,基本上以文学评论为主,后来出版过两本著作,一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另一本是《躁动与喧哗》。我不太清楚别人的知识背景,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受别林斯基的影响很深,无论是他的文章风格,还是他对俄罗斯的深厚的感情和关怀,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在。后来有些人批评别林斯基,坦率说,我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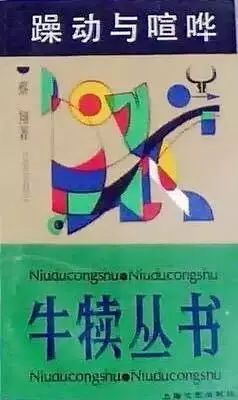
《躁动与喧哗》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
一方面,1980年代,尤其在文学批评领域,好像是一个没有规范和家法的年代,每个人都在突出自己的个性,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隐约其中的,或许正是吉登斯所谓的“解放政治”。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也难免逞才使气,语不惊人死不休,以辞害意也是常有的。
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走进1980年代,并且努力塑造着1980年代。一个人和一个人不一样,一代人和一代人也不一样。对我而言,被唤醒的,可能是1960年代的记忆,这一记忆被压抑在1970年代。那或许是一种有关青春和激情的记忆,一种解放和抗争的记忆,也可能是一种重新创造世界的记忆——有关这一切的记忆,都隐蔽在共和国的理念之中,或者,我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革命”的理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1980年代也是对这一理念的遥远的回应,尤其是有关“异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暗暗接通了1960年代的血脉。因此,1980年代,在它拒绝政治的时候,却隐伏着另一种重新创造政治的愿望,这可能更重要。但是,1980年代毕竟有着它的规定性,尽管1980年代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在1960或者1970年代找到它的历史缘起,但仍然不能完全说明1980年代的重要意义。1980年代的重要性仍然在于它处在“两个三十年”之间,它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的历史意义,至今也仍然难以估计。然而,这一转折的最终完成,却是因为各种的因素,甚至包括偶然的历史机遇。而在这一历史机遇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学的介入。一些历史事件被重新解释,比如“五·四”,“个人”再次成为一个统治性的概念。所谓“现代化”,也更多地被技术化,或者可以称之为“技术现代性”。正是“技术”(科学)的介入,这一所谓的历史转折才可能完成,显然,技术崇拜——科学崇拜——制度崇拜——意识形态崇拜,也正是1980年代的逻辑演变,这一逻辑帮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中。尽管不可能每个人都被这一逻辑吸纳,但仍然可以看出一种大致的变化。
因此,一方面,1980年代在努力回应“革命”的理念,另一方面,又中断了这一“革命”的逻辑发展,人们试图找到另一种逻辑起点,“社会主义”被简单地解释为“封建”和“人治”,而“1980年代”则被理解为“现代”和“法治”。所谓重新“创造政治”在这一逻辑的裹挟之中,除了继续的“西方化”,似乎也很难找到自己新的形式化的可能。我想说明的是,尽管如此,1980年代的文学仍然呈现出一种抗争性的态势,它似乎并未心甘情愿地被这一“现代性”所“启蒙”,但是却逐渐退回到审美的领域,个人始终被强调,并抗拒一切的规范、约束和异化的可能,但并不是在政治领域,而是在美的领域。正是在这一领域中,同时生产出了一种巨大的幻觉,当然,幻觉依然可以生产激情,甚至理想主义的激情。
1980年代发生了许多事情,因此,这一时代就不可能被完全地做一种扁平化的处理。对我来说,1984年也许非常重要。“个人”的迷狂并未持续太久,“文化”这个概念开始引起我的兴趣。尽管,在当时,这个概念仅仅停留在人类学的层面,但也足以引发我们继续的思考。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机械的二分法,已经无法继续吸引我们,“文化”恰在此时打开了另一个广阔的领域,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这个概念可能悄悄地重新接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不再处于世界的中心,历史、国家、族群、甚至社会现实,都在这一关系领域中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一种记忆,一种有关1960年代的记忆也再次被悄悄唤醒,只是那时并未自觉地意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中,有一篇文章叫《知识分子和文学》,其中说到:“当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已经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且开始分享权力和财富。当知识可以同权力和财富进行等价或半等价的交换时,它还能保持自己‘现状反对者’或‘社会良心’形象吗?”二十多年后,不幸而言中。当时有意识的,可能是“文化批评”这个概念,《躁动与喧哗》一书中,收录了我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爱莲女士的一次对话,在对话中,我强调了“批评如果能够进入了文化层面,前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而在方法论层面,则更强调“为什么这样写”,当然,总体上仍然局限在一种“个人化”的立场:“它主要立足于人文精神,再具体地说,是它的个人化立场,它从个人主体的角度自觉地反思或展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这也是我们这个是时代的精神反映”,这就是1980年代对我的启发和制约,它和后来的“文化研究”并不完全一样。重新翻阅旧著,我曾有一篇文章名为“神圣启示录”,里面粗糙地讨论了“文革”,也完全受制当时的思想氛围,但却强调了“重建信仰”。
1980年代终结于1989年,但在1989年之前,却已经出现了某种疲惫的情绪。创造的激情开始冷却,怀疑和自我怀疑再次出现。我之所以要提出“之前”,因为我反对把一个时代的终结直接归之于某一政治事件,那样只可能束缚我们的思考。但是,1989年却把这种情绪强化了。但反过来,也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想,包括更广泛地阅读。
1989年之后,我的写作范围开始扩大,但基本上仍然延续着所谓的“文化”。我讨论过武侠小说,后来结集为《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有几年,沉迷于古代,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所谓的学术小品《自由注解》,另一本是《此情谁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当然,这些文章搁到今天,我未必敢写,也正应了俗话,读书越多,胆子越小。但在那个时候,多少有一种重新反思1980年代的愿望在内。而在1994年,我出版了《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那是一本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1980年代的浮华之气略有减退。相反,可能更多的,是疑虑重重,以及再次奋发的希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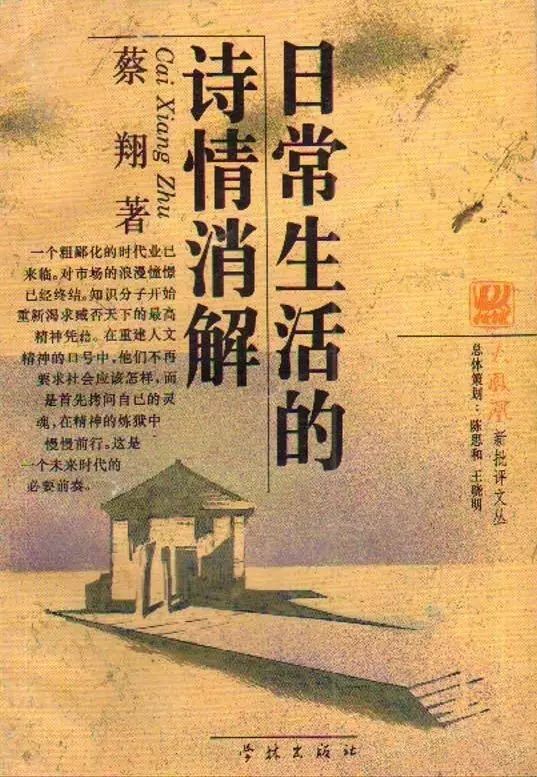
1990年代,我很少写作当代文学最新作品的评论,一方面,我觉得不断地追踪新的作品越来越困难,而另一方面,我一直隐隐地抗拒文学批评的职业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自由写作者”,所以在1990年代的后期,我基本上从事两方面的写作:散文和随笔。后来,散文结集为《神圣回忆》,随笔则命名为《回答今天》。
对我个人而言,1990年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1980年代,尽管至今我仍然难以描述这个年代。但在那个时代,一种批判意识开始重新确立,并强调“批判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我的确不太清楚应该如何描述这个时代,但有一点,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会将这个时代解释为一个“小时代”,一个不断向内又不断缩小的时代,一个模仿和复制的时代。
我也许应该提到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一书,这本书1990年代中期出版于香港,但通过各种管道进入大陆。书中的一些作者都是我在1980年代的朋友,我一方面感叹于他们在学术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性的重新讨论,将“社会主义”从一度流行的“封建”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从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讨论空间。当然,我也有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过于的“现代”,而忽略了“革命”的特殊意义。可能,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会写《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的原因之一。

但是,1990年代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可能是现实的急剧变化,这一变化才真正使我们从1980年代的幻觉中走出,直面现实。隐秘已久的1960年代的记忆,这个时候才可能被真正唤醒。1996年,我写作了《底层》一文,很多年后,也就是2006年,我在《何谓文学本身》一书的自序中,回顾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前后:
大概在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底层》的散文,在那篇文章里,我记录了当时的感想和感受。今天,“底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泛化的语词,而且,开始进入学术讨论的视域。我无意把我当年的那篇文章纳入这一知识谱系,事实上,今天相关的学术讨论与我这篇文章也没有丝毫的关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活动。在这里,我重提旧事,只是感慨于现实的残酷性程度,正是现实的残酷,才逼使这个词浮出水面。在学术研究的热闹背后,却是一个阶级的日益贫困和更加不堪的生活状况。每念及此,常常感慨万千。
……可是,我仍然得面对这个语词,不仅因为这个语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现实,而且,我们还得面对因为这个词而导致的各种批评意见。而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批评意见居然主要来自于文学批评届。或许,因为这个词的粗暴进入,破坏了文学的所谓的美和诗意,破坏了文学久已习惯的想象方式?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似乎是,似乎也不完全是。
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还是这样一种意见,今天重提“底层”的目的何在?的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不能也不应该漠视底层以及所有弱势阶层的存在。我们必须确立一种这样的社会原则,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应该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普遍的价值诉求,甚至成为“政治正确”的核心内涵。
也许,《底层》这篇文章,暗示了我的一个新的写作时代的开始,只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很多年后,也就是2009年的夏天,我应李云雷兄之邀,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他主持的一个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会,在会上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正式用过“底层文学”这个概念,而且,坦率说,我对这个概念有点疑虑,也是在那篇自序中,我提到:“然而,在文学的意义上,我的态度却会更加谨慎。因为‘政治正确’并不可能保证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这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常识。如果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即使把‘底层’当做题材,那么它也永远无法替代文学的其他叙事元素。‘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应该成为一个次序先后排列的问题,它们永远复杂的纠缠在一起,共同完成文学的叙事过程。在我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的叙述底层,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可是,我仍然支持这一写作倾向,我的意思是,这一文学写作倾向最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有益的启示:
一,重新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视野,并挑战心理主义的霸权地位;
二,重新讨论个人和所属族群的关系,并挑战个人中心主义;
三,重新讨论私人情感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挑战泛滥化的审美主义倾向。

当然,更重要的是,并不是就此轻易地否定心理主义等等,而是如何在这数者之间构置一种必要的张力,当然,在我看来,所谓“底层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如何创造一种重新解释世界的思想,否则的话,即使“批判现实主义”,也可能无奈地默认资本逻辑的合法性。如此这样的话,那么,“底层文学”的意义就值得怀疑。
我在《何谓文学本身》的自序中,也曾回顾了近十年来的思想路程:
“对我来说,近十年的道路,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转型的痛苦,内心更充满了困惑、焦虑甚至分裂,许多的想法沉入心底,成为隐密,难以言说。正是在内心的隐密深处,一些确立已久的信念开始动摇,而另一些曾被压抑许久的记忆却又渐渐复活。在许多的时间里,我默默注视自己,一个暧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我曾经一度想放弃写作,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述这个暧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直到今天,这种想法仍然挥之不去。我不知道我的写作的意义何在,甚至有无意义,而在二十年前,这却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写作前提。”
不过,仍然没有放弃寻找。重要的,可能是“文化研究”这个概念的出现,同20年前的泛化的“文化”概念相比,“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性,而且指向明确:“另一些语词却在这个时代愤怒地涌现出来:资本、权力、阶级、市场……等等我们与这些语词遭遇,与这些语词背后的残酷的现实遭遇,现实逼使我们重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或部分的接受所谓的‘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的需要,更多的,仍然是现实使然。是我在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确立过程之中,渴望找到的某种理论资源或者写作范式。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我,或者对我的朋友来说,‘文化研究’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能指’,我们依据这个‘能指’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叙述,包括对文学的叙述”。就我个人而言,这一所谓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西方理论的背景,而是有可能接通我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包括国家、阶级、公平、平等,等等。实际上,有关“纯文学”的讨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当然,我并不排斥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相反,我愈加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而在理论转型的同时也正是知识和学术的转型。
2002年,我调到上海大学工作,学院给我一个新的专业化的工作环境。授课、读书、讨论、写作……,几乎构成了我全部的生活内容。在这一环境中,我开始把我的经验和感觉知识化,也开始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研究。
上海大学

有几年时间,我的工作内容完全围绕重新讨论“十七年”的文学和文化想象。方法论上仍然延续了我在二十年前所希望的“为什么会这样写”的讨论理路,而在具体讨论中,则基本上让文学史和社会史处于一种互文性的叙述之中。就像我过去也曾经说过:“这些讨论既在文学之中,又在文学之外,这和作者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打通文本内部/外部的研究有关,也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新的实践。显然,作者努力使文学重回公共领域,因此,文学史始终处在和社会政治史积极对话的过程中间。作者在强调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同时,并没有刻意回避无理性的一面,而是严肃讨论这一正当性如何或因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也从不认为只有一种最好的研究方法,但在这本书中,我更愿意采取这种方法。
实际上,随着讨论的进一步展开,我愈加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只要我们不满足于既定的世界秩序的安排,而且愿意继续讨论“世界应该怎样”,那么,这就是政治的。所以,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
当然,对我来说,“文化研究”只是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论上的过渡——“如果哪一天,‘文化研究’控制或者开始限制我的思考,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它”。今天,我仍然是这一看法。
我在最近完成的著作《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的导论中谈到:罗兰·巴特在《共产主义的设想》中以一种决断性的修辞方式阐释了西方左翼在今天的命运和工作:“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贴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众多而丰富的19世纪现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青年人群众大部分所秉持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探索表达共产主义设想的众多小团体的实验精神,也是受群起之功、被围追堵截的实验精神……无疑就是这种情况,和19世纪一样,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共产主义假设的胜利,而是它的存在条件。处于目前压倒性的反动间隔期之中,我们的任务如下:将思想进程——就其特质而言总是全球化的,或普遍的——和政治经验——总是地方性的和独一无二的,但毕竟是可传播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共产主义设想得以复生,既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也在这片大地之上。”在某种大致的也是粗略的意义上,我可能倾向于巴丢的说法,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回到19世纪?没有别的路径,我们只能带着20世纪的思想遗产——这一遗产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包括20世纪的失败教训——回到19世纪,重新的思考、探索和准备另一个世纪的到来——也许,这个世界遥遥无期。但是,也正如鲍曼在《寻找政治》中所言:“知识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对它做何种使用。归根到底,这事关我们自己的选择。然而,没有这种知识,任何选择就无从展开。有这种知识,自由人至少有行使其自由之机会。”

罗兰·巴特

鲍曼
在这一意义上,我开始注意并重视学院的知识生产的工作。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讨论1980年代,也许,我对1980年代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之后,才可能较为完整地描述这一“六十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我不会轻易地否定1980年代,实际上这一时代的复杂性并没有在我们的叙述中被完整的再现出来。我也不会轻易地否定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概念:民主、自由、个人、法治等等。相反,我一直努力把这些概念纳入到我的思想谱系之中,并和其他的概念一起构成对世界的设想。
我亲历并见证了这一“三十年”的变化,我也一直在寻找通向未来世界的道路,这一寻找隐蔽在1960年代的记忆之中,至今,我也并未放弃这一寻找,尽管寻找在今天变得怎样的困难重重。我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老去,但在内心深处,仍然回荡着少年时代的呐喊——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始终是共和国的长子。



本文原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蔡翔卷》的序言。2012年,台湾人间出版社编选《神圣回忆:蔡翔选集》收入此文。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明日推送:
布迪厄:性别结构与女性处境
或许你还想看:
本期编辑
绛芸轩

微信号:Wenyipiping
微博号:文艺批评Wenyipiping
IPHONE用户
由此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