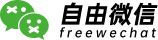其他
导言2024年6月28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通过,为继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指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谁来带动乡村振兴?《乡村纪事》一书集合了多位作者在新型集体经济主题上的探索,尝试回答这一问题。通过集体调研、集体写作的方式研究村庄的集体化实践,讲述七个真实的乡村故事,作者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农村振兴发展的内在力量,是重新激活的村集体。乡村要发展,不可能依靠分散的小农户,也不能只依靠某个“能人”和大户,更不能简单等着资本下乡或城市的反哺输血。村民要真正组织起来,在村集体的领导下,以整体的角色投身到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的潮流中去,真正把握住振兴发展的主动性。本文选编自《乡村纪事》序言,主要结合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阐释:一、为什么乡村振兴的龙头是村集体,而不是政府、个体农户或者资本?二、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集体组织者如何带动村民突破长期的分散惯性和阻力?本书中的七个集体经济案例虽然在产业基础、发展过程、发展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只有付出逆市场化的努力,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创造“合”的条件,才能带动群众,让村民们逐步脱离“分”的惯性,创造新型集体经济。新型集体化实践2018年夏天,我们前往西藏自治区双湖县调研嘎措乡集体经济,刚开始当地的一些干部对我们调研集体经济有些不解。他们认为集体经济是落后的、迟早要被淘汰的制度,有什么值得调研的呢?但我们调研发现,恰恰是集体经济让嘎措乡拥有了稳健的经济、小康的民生、和谐的社会、以及良好的生态。与单干牧户相比,在接近无人区的雪域高原上,嘎措的集体牧业既能保护生态,严格执行草场轮牧制度,又能出产更优质的畜牧品,还能开展多元兼业,自主开发多种皮毛制品,组织建筑队,等等。嘎措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远高于双湖县的其它乡镇,还高于西藏双湖县以外地区农牧民的人均水平。在社区内部,嘎措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照顾年老体弱者,甚至还首创了牧民养老制度。嘎措乡地处海拔4900米的高原,自然环境恶劣,除了“生态宜居”这一条非人力可为之外,依靠集体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其他几项: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我们在西藏听到的有关集体经济的成见并不罕见。这种成见大多随着农村改革、集体式微而出现,时至今日仍然有相当的普遍性。农村改革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小农持久论,倡导小农是“三农”发展的主体;另一种是“腾笼换鸟”论(或称小农消亡论),倡导农民进城、资本下乡,让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成为农业的主体。那么,乡村振兴应以谁为龙头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农”困境已经说明乡村振兴的龙头不可能是分散的小农,但也不是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此外,乡村振兴也不能简单依靠城市化来带动,乡村问题与城乡关系、城市化密切相关,但也是相对独立的,政府也难以充当乡村振兴的龙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已经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放了大量的资金,这样的外部性输血对改变乡村面貌,尤其对改善基础设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然而仅仅依靠政府并不能解决农村社区由去组织化带来的内生性缺失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政府已然看到乡村问题的基础性和长期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个中长期战略,正是体现了这一认识。我们希望通过调研回答乡村振兴谁是龙头,乡村振兴如何探路这两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乡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短板是缺乏组织化、缺乏内生性。通过调研,我们认为重新激活的村集体应该成为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龙头,村庄的新集体化能够解决乡村的组织化和内生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村业态黯淡、农村社区原子化、农村生态环境缺乏整体性统筹等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乡村振兴才有基础和抓手。高寒地区牧业大多面临“过度放牧—草地退化—牲畜减产—牧民致贫”的循环。[图源:Unsplash]乡村振兴的龙头谁是乡村振兴的龙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缺乏抓手,面对扶贫增收的任务,地方领导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安排农民的种养项目,结果却往往不如预期。行政命令式的推动往往效果不佳、事与愿违,还可能导致相互的埋怨和腹诽:地方领导责怪村干部落实不积极,村干部则觉得自己要被动承担试错的责任和后果,担心遭到村民埋怨。显然,地方领导做主,却并不承担决策的后果,村干部不能决策,却要承担试错的后果,权责不统一。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龙头不应该是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村集体。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发展的战略指引,而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法和决策,需要依靠村集体发挥责任心和能动性。资本是否能承担乡村振兴的主体呢?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一些资本活跃在民间高端论坛,在乡村振兴中寻求商机。诚然,让资本唱主角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的主流思路,然而招商引资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性。有国际农政研究发现,资本化农业越来越趋向于“采掘性”(extractivism),即农业越来越脱离传统的资源循环模式,越来越趋向于资源流失的模式,这样的农业模式具有采掘性,也可称为“掠夺式”。印度著名的生态学家范达娜席瓦言简意赅评论了其后果:在所谓高产的同时,整个生态系统在沉沦,生态的多功能在沉沦,每亩的营养产出在下降。在所谓高产的同时,它们把高产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费450亿美元才能清除,而这些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荷兰农政学者范德普勒格指出,资本主导的农业在表面上、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了“发展”,